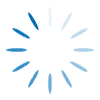“西格德夫人,你知道该怎么做。”棕发男人甚至都没从那张照片里抬起眼。
女孩不安地坐在长椅上,周围穿黑皮大衣的人来去匆匆,她穿着裙子坐在这里,像只误入狼群的小鹿。金发女秘书踩着高跟停在面前:“上校非常忙碌,无法见您”。
不过一句话功夫,眼泪就从她脸颊滚落下来。
棕发男人在一群下属簇拥下走过回廊的时候,恰恰看到了这一幕。
这就受不了了?我们的小夜莺…几天没投喂,就找不到别的枝头唱歌了?
君舍才从会议室回来,内线又响起来。
这次是副官的声音:“长官,利达小姐…她找到我这边,哭得很厉害,坚持要见您一面,说…只要五分钟…”
他甚至能想象电话那头,副官如何被抽噎的女人缠得手足无措,而那只西西里小兔又怎样语无伦次哀求着那微不足道的五分钟。
“海德里希,你什么时候降级成传话邮差了?”
黑发女孩终于被“请”出了总部大楼。
巴黎善变的夏日都像在附和她,天空暗下来,轰隆隆几声闷雷,起初只是雨点,很快便织成密密的雨幕,砸在窗台上,石板上,稀释着这食人魔窟常年弥漫的血腥气。
男人修长手指挑开窗帘一角。
那个小小的的身影果然还在那里,裙子都湿透了黏在身上,失了魂似的呆呆立在小广场中央。
如同被暴雨从枝头打下来的小雀鸟,羽毛凌乱,随时可能断了气。
连日以来的浮躁莫名就熨帖了些。
这是种久违的感觉——他本该驾轻就熟的,只需一个眼神、一句话,就能决定一个女人该如沐春风还是如坠冰窖。从前在柏林在华沙,他一向乐在其中,那是权力和杀戮之外,最轻易就能攥在手里的快意,廉价却上头。
他忽然明白自己此刻需要什么。一些掌控,迫切地需要,就像驾驭烈马就像扼住咽喉。
尤其是自那晚救生艇上的一幕幕钻进脑子里,那些他从前只觉得荒唐矫情的东西,如今却敢在深夜反复闯进来,嘲笑着他,蔑视着他。随之而来的极度不快,让他总想即刻想碾碎什么、撕毁什么。
而看着雨里为他哭的小家伙,那种触不可及的躁动,竟真稍微平复了些。
…..
烟雾在酒店套房里缠绕、扭曲,那廉价香精味儿终被冲淡了些。
男人深深吸了一口雪茄,让辛辣在胸腔里打了个整转,试图压下那点因这回忆升起来的躁意。
可烟雾没散多久,脑海里那个浑身湿透的小东西又与另一个影子重合起来——一会儿站在华沙春雨的街边,一会儿躺在被浪涛打湿的小艇上。
月光底下,苍白的小脸湿漉漉,即使奄奄一息也呢喃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,而醒过来,那双黑眼睛里,又偏在绵绵软软底下,藏着若有若无的不服,勾得人心尖发痒发胀。
他猛然摁熄了烟。
像是方才味同嚼蜡的情事耗尽了最后一点耐性,男人重又扯开领口,径自走向酒柜,取出一瓶白兰地,连杯子都懒得找,仰头灌了一大口。
液体灼过喉咙,却没能驱散空洞,反而让一种更该死的无聊感翻涌上来。
他需要一点,一点立刻可得的、驯服后的温顺,只要他抬抬眼,对方就会乖乖凑过来,把一颗心都捧给他。
男人放下酒杯,看了眼日历,那演出好像就是明晚?
火候差不多了,再饿下去,鸟儿就该忘记怎么唱歌,甚至忘记该怎么讨食了。该去收网了,正好看看被泪水和雨水泡过的心,是不是会变得更柔软听话些。
——————
红磨坊的标志性风车在巴黎的夜雾中转动,霓虹灯牌闪烁着,像一颗颗跳动不休的心脏,把周遭笼罩在一片醉生梦死里。
俞琬捏着手里那张请柬,深吸了一口气,才跟着人潮走进这鼎鼎大名却让她有些无所适从的地方。
她本来不该一个人来的。
那天诊台后,利达塞给她两张连座票,眼睛亮晶晶地求她一定要过来看,说这是个新舞种,是更有生命力的舞。她应下了,还有隐隐的期待。
在离别已然进入倒计时的日子里,能同克莱恩和寻常情侣一样再看一场演出,从他越缠越紧的军务绳结中偷得须臾时光。哪怕多一分、多一秒,都是好的。
可傍晚的一个紧急电话,却把克莱恩直接叫去了机场——盟军在法国西北诺曼底或有异动,所有上校以上的武装党卫军指挥官必须火速奔赴柏林参会。
男人表情当时就凝重了,在“狼来了”无数次后。那些英国人和美国人终于要动真格了。
显然她来不及再找其他人同行了,男人歉意地吻了吻她的额头,嘱咐她一个人就别去那种地方,可俞琬思索了很久,还是决定过来看看。
这是利达第一次做主舞,她爱跳舞,又那么重视这次演出,她不想让朋友失望。
红磨坊… 那是个承载着巴黎人夜生活缩影的地方,饶是在报纸上里看过,也听病人说过了无数次,可她还没去过呢,说到底对那里的热闹也还是有一丝好奇的。
巴黎和华沙不一样,才带着警卫在大厅走上几步,周遭无数道目光就打过来,好奇的,警惕的,窃窃私语织成一张网,裹得她有些窘迫。她从不习惯成为人群的焦点,便让“小尾巴”去门口呆着。
可才独自落了座她就后悔了。
女孩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,像一株迷失在热带雨林的幽兰,局促地坐在观众席前排,手包攥在膝头。
这里到底和歌剧院不同,没有包厢的分隔,目之所及都是中下级军官和大腹便便的绅士,臂弯里无不挽着精致的女人,或低声说笑,或相互依偎,成双入对的。
这么一衬托,就显得落单的自己像个异类了。
这种无所适从,在灯光暗下来后才好了些。
喧嚣渐息,帷幕拉开,这表演和她看过的所有舞蹈都不同,既奔放又压抑,每一次跳跃都像在嘶吼着什么,让人屏住了呼吸去听。
在利达戴着面纱登场的那一刻,女孩连最初那份拘谨也忘却了。
台上的她变了一个人,不再是初次见面那个风一吹就要飘走的的女孩子,像是有什么要从她身体里破茧而出似的,就连自己也感觉到那力量了。
可就在第一幕结束,一股凉飕飕的感觉突然从背后爬上来,像毒蛇信子扫过皮肤,又冷又黏。
不舒服,但很熟悉。
她下意识的往后瞟,入口处的光影里,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闲庭信步进来,又在后排角落坐了下来。除了一双苍白的手,他几乎整个人融进了黑暗里。
那步态有点像谁…可太黑了没太看清。她假装整理裙摆,透过座椅间隙看过去。
那双眼睛…是君舍!
女孩赶紧转过头,正襟危坐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